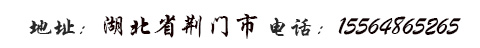淄博作家忆年俗宋以柱过年吃的肉
|
本文转自:鲁中晨报 每年旧历的新年,到了腊月廿八日落之后,爹娘就开始炸菜了。那时炸菜,不止是炸肉炸鱼,还有炸萝卜丸子、炸豆腐,其他好像就很少了。 整个下午,爹娘都在做炸菜的准备。膝盖高的生铁锅,倒了半锅大豆油。杀鸡是爹的活,左手攥住鸡翅,伸长了拇指、食指,捏住鸡冠子,向后拉起,右手握菜刀柄,拇指、食指捏去几根鸡毛,用刀刃在鸡脖子上迅疾一划,扔到南墙根,由着鸡去扑腾。有的鸡,还叫几声,站起来挪几步,喝了大酒一样倒下,把腿和翅膀慢慢伸开去。 娘剪了指甲,净了手,头发扎好,挽起衣袖,静静坐在矮桌前,手执菜刀,把鸡的肉、猪的肉切成二分之一糖块大小,小咸鱼切成细长条,豆腐斜了刀,切小四方块。娘拿出六个鸡蛋,想一想,又放回一个去,见我在看她,红了脸,笑一笑,说:“留下一个,明天早上给你爹烫了喝。”鸡蛋打碎,掺面粉、水,和成稀糊。炸菜时,拿筷子夹了鸡肉猪肉鱼肉,在面糊里打个滚,放到起油浪的油锅里,“嗞”一下,肉翻几个跟头,面糊变鹅黄,香味钻出来,执笊篱小心捞到瓷盆里。瓷盆底下铺了几张煎饼,吸干炸肉上的油。这煎饼叫油煎饼,出去正月,炸肉吃完了,可以吃到油煎饼。油煎饼,浸透了油,很香,很硬,咬不动,像啃骨头,吃两手油。开水泡软,煎饼和油的香味一块出来。 炸菜的过程,都是娘在下肉、捞肉。爹只蹲在一边看,卷纸烟,回北屋喝茶水,给娘端杯水。看着面糊起了黄色,就喊:“快捞,快捞,煳了。”娘就不愿意,说:“不能说煳了。”我和妹妹要是在家,也是隔了很远站着,听到娘说的话,赶紧讨好地大声笑一笑。 从一开始炸菜,我和妹妹就不能靠近油锅旁,甚至不能在家。那时,爹娘的理由是,离油锅远点,要是有别的孩子来,赶紧一块出去玩。要是陌生的孩子进来,就会踩油锅。那油锅里的油,顷刻间烟消云散,一点儿也没了。打小知道油的珍贵,大多就听话地出去,直到夜幕罩下来,估摸着爹娘忙完了才回家。 走进柴门,满院子都是香气,撞得鼻子疼。但你别想吃上一口,哪怕一块炸肉掉到地上,娘也会立即弯腰拾起来,放到嘴边吹一下,放进盛炸菜的瓷盆里。金黄的一大盆,长的,圆的,方的,滴着油,香气如缕,丝丝不绝。因为这香味,我常睡不好觉,生怕给老鼠偷了去。娘却不担心,告诫我只要你别说,老鼠就不会知道。我就满怀疑惑地睡去。 那时家里收入很少,过年的时候,爹娘也不会亏待我和妹妹,买鞭炮,买花,尤其是,能狠狠地吃上一顿肉。小时候就是馋肉。瞧瞧,火炉上的大铁锅里,沸腾着的,翻滚着的,油浪裹挟的,正是一块块肉骨头,好几种骨头煮在一起,猪骨头,鸡骨头,或许还有娘故意落下的一个整鸡腿。年景好一点,爹就在骨头锅里加上猪皮、猪耳朵、猪嘴、猪尾巴、猪肠子,一块炖,那不是在煮骨头,就是在煮肉,哪用什么花椒茴香葱花姜,只需要一把大粒的盐。汤白肉红肉白。 爹生怕骨头上的肉不好啃,有意多煮上一段时间。爹不停卷烟,喝大把抓茶,我和妹妹使劲等着,简直是在咬着牙等肉熟。鞭炮不想放,坐又坐不住,和锅里翻滚的肉骨头一样,我和妹妹两个小身子,倚在床边翻来滚去。一次次偷看着锅上边的雾气,透过雾气去找肉骨头。肉汤里的骨头往上一跳,落下去,往上一跳,落下去,像沂河里白色的窜条鱼。我不敢使劲咽唾沫,佯装咳嗽一声,赶紧把满嘴的唾液咽下去。 爹把锅端到桌子边上,端起一个碗,用筷子夹满骨头,又拿起一个碗……朝我和妹妹喊一声,赶紧过来吧。看着我和妹妹手里拿着骨头了,又说,别乱说话,赶紧吃。好像一开口说话,那肉就能飞了,就像炸菜锅里的油。啃骨头、吃肉快,咬着舌头是经常的事,咬狠了,也不敢说或者哭,忍着一包泪水,狠狠地吃肉。爹只是捡一点肉不多的骨头啃。娘则干脆不吃,不爱吃,我和妹妹不相信。被爹吼一句,别乱说话,吃。 从炸菜开始,院子外的柴门是早就锁好了的。 吃饱了,待在家里玩,别出去疯。爹不让出去。爹是怕我们出去炫耀吃肉了。 到床上躺着吧。让肉在肚子里多待会儿。娘总是那么温暖,笑嘻嘻的,娘怎么不吃肉呢?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和妹妹已经不在意爹娘炸菜、煮骨头了?家里收入多了,每年爹娘总是笑嘻嘻地煮肉,猪肉捡好的煮,鸡整只煮,满屋子满院子的香气,反而不太在意了。娘的胃不好,只能吃一点点。我和妹妹是一点也不吃了。大部分就放在那儿。爹为了鼓动我们吃点,就讲了一个故事。 他在生产队当会计的时候,每到年终岁尾,队里为了感谢大家一年来的劳累,会割上几斤肉,用白菜、粉皮炖了,让大伙好好吃一顿。在氤氲的香气里,大家手上动作都格外麻利。不断拿负责炖肉的狗头军师开玩笑。待到白菜粉皮肉锅一下炉子。队长立刻让大伙停下来,别干了,别干了,装啥呢装,哈喇子都淌到锅里了,小心给我干坏了活。大家笑着,迫不及待地围在一起。队长举起盛酒的茶碗,就是不喝酒。大伙就呆着脸看。好一会儿,队长说:“一气喝完这一茶碗酒,然后,把油灯吹灭,吃菜。”这已经是习惯了的游戏,怕馋鬼专门拣肉吃。大家笑哈哈的。在黑暗里,只听到筷子的碰撞,快速地咀嚼,还有一阵嚷嚷:“谁把我的筷子夹住了。”大伙就借机放松下来,猛笑一阵。 吃得差不多了。点上灯,大伙用菜汤泡窝头。一边互相打听吃肉的多少。这个几块,那个几块。只有三叔默不作声,只在那儿笑。后来,三叔忍不住,和父亲说摸黑吃肉多的秘诀,大幅度撑开筷子,伸到盆里,慢慢收拢,收拢来后,使劲夹。白菜、粉条熟得快,很容易夹断,夹不断的就是肉,尽管吃。爹试过,很灵,比别人吃得多。 现在呢,像小时候那样,坐下来,郑重其事地吃,也吃不了几块肉。 作家简介: 宋以柱,乡村教师,淄博市签约作家,山东省作协会员。出版《旗袍》等五部小说集,长篇小说《黑蜻蜓,白蜻蜓》一部。作品获淄博市文学艺术奖、淄博市精品工程奖、第九届小小说金麻雀奖。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aohuixianga.com/xhxyfyl/10927.html
- 上一篇文章: 火宫煮盘盘麻辣烫找回市井烟火气
- 下一篇文章: 来山西,体验另一种炫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