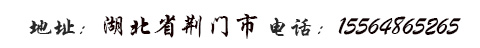农村的吃食
|
在我的记忆当中,农村人整年为一口吃食而劳累,饿肚子的年代早已远去不复返了。缺衣少穿这种基本的生存困境也仅存在爷爷辈偶尔的唠叨叙旧中。 民以食为天,农民天生的使命就是种地打粮,这种世代延续的生存之道融入到一代代农家子弟的血液里。无论走到哪里,我们对土地都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心里始终装着一个田园梦。 在农村,基本所有的生活都在围绕着农事转,吃饭也必须是,农忙时,吃食要求能迅速填饱肚子,补充能量,小麦这种粮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白面馒头,白面面条绝对是农村饭桌上的“主角”。 (一)主食篇 能成为主食的粮食有很多种,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出现最多的有三种,黑面馍,高粱面做的,黄面馍,玉米面做的,白面馍,小麦面做的。在小说孙少平的那个年代,农村吃的最多的是黑面馍,还吃不饱。在爸妈那个年代,他们对小时候常吃的红薯片面馍念念不忘。 七八十年代的黄土高原和豫东平原的农民主要的吃食不相同,但都说明了白面馍是很难吃到的,只是到了过年,家里可能买上几斤白面包一顿饺子打打牙祭。 有人说,为什么不吃大米? 现在,唯一能和小麦一争高下的粮食就是大米。 也有一种现实,哪个地方产什么,哪个地方的人们优先吃什么。大米的主要产地在南方,是水稻,北方也有旱稻,比如东北大米,原阳大米。豫东主要粮食作物是小麦,这里的人们还是以小麦为主。 还有,大米的价格一直是小麦的数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们这里的人们更喜欢小麦这种粮食。大米也吃,不过是偶尔一顿的蒸米饭,很多次的大米稀饭。 小麦快成熟的时候,农村人喜欢薅两把麦穗子在煤球炉子上烤,烤焦黄了,搁手心里一揉一搓,憋一口气使劲把麦壳吹走,两手左右倒腾麦粒,少量的壳皮靠着两掌之间的对流形成的风,四处散落,直到手心里全是脱了壳的麦粒,左右手各留一把,往嘴里一送,上下牙反复咀嚼,甜甜软软带点青涩味的麦汁就进了肚。 洛阳有些地区,喜欢用这时候的小麦做捻捻转儿。 就是先把籽粒饱满,刚刚硬粒还略带柔软的大麦麦穗割回家,搓掉麦壳,用筛子、簸箕等把麦粒分离出来,然后用锅把分离的麦粒炒熟,晾凉,接下来把晾凉的麦粒放入石磨中磨制,石磨的磨齿中便会挤出来缕缕长约寸许的面条,这些青面条子可以炒着吃,大多时候是放入碗中,加入黄瓜丝、蒜苗、麻酱汁、香油醋、蒜末等调料凉拌。 我们这个地区不做这种流程复杂的吃食,而是等小麦收割脱粒后,在太阳底下暴晒,晒到麦子上全是阳光的味道,放到嘴里咬一口硌牙,一部分麦子收进麦囤里,埋几包麦药,预防生虫,另外一部分卖掉换钱,往往还会预留几袋。 新粮下来了,家里的妇女们要忙了,忙着用簸箕筛子簸筛粮食,也就是把粮食里的土粒,石头粒挑出来,再泼上点水晾大半干,家里的男人们拉着半袋装的粮食去磨坊打面。磨出来的白面也就是好面,是我们主食的原料,脱壳后出来的叫麦麸,麦麸是喂养猪鸭鹅的主要辅料。 有了面粉,农村的妇人个个变成了巧妇,发面蒸馒头,馒头可以是方可以是圆,要么切点葱花,卷成油卷,要么准备点韭菜粉条包点包子,有娃娃的人家常做糖包。这一切吃厌烦了,揉点面烙油饼,和盆面糊摊饼吃。 以上这些一般作为早晚的主食。中午,我们这个地方的老乡最爱吃面条,春秋冬是汤面条,简单点,提前腌制半碗葱花,等面条熟了之后倒进去,滴几滴香油,葱花面就好了,喜欢吃鸡蛋的,可以提前打进去几个。复杂点,炒点番茄,搁点肉丝,番茄肉丝面,城里称这种面叫炝锅面。 汤面适合天凉吃,暖胃。夏天,我们最爱吃的是捞面条,面条煮熟后过一遍凉水,再添半盆水凉水,吃的时候直接用筷子捞。半炒锅水烧开,放一大把荆芥,搁点调料,另用蒜臼捣点蒜泥。凉面条,荆芥汤,蒜泥三种食材搭配到一个碗里,清凉可口。两大碗下肚,还可以喝半碗浓稠的面汤。 还有一样传统的食物是用小麦粉做的,饺子。不过这种吃食平常很少吃,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平常农忙没那工夫,春节,一家老小都在家,饺子是包了一锅排又一锅排。 中秋节,我们这个地方流行做火(tao)这种面食,它类似于城里寻常见的圆烧饼,城里的烧饼是烤熟的,老家的火(tao)是蒸熟的,里面可以夹心糖或者葱花,正面要用顶针按下一个个圆,寓意团圆。 我们小时候,零食还不普遍,为了怕孩子屈嘴,家里的妈妈经常和面炸点麻叶或者麻花头。我们还喜欢吃焦疙瘩,就是蒸馒头的时候,贴近锅边的馒头底会被烧焦,把焦疙瘩抠下来直接咬着吃。 豫东还有一种面食比较高大上,那就是高炉烧饼。每个村的每个集都会有一家甚至几家打烧饼的。一个像鸡窝一样的炉子,炉底放的是木炭,炉顶贴的是烧饼,烧饼烤熟之后,用两个长铲铲下来就可以卖了。 此饼多以发酵面制作,配有芝麻、五香粉和糖稀。擀片包芯,砍花摊圆,然后单面沾芝麻贴烤。成熟后外酥里嫩,可单食,也可夹食,我们最爱的莫过于烧饼夹肉。 你们有印象吗?当年红得一塌糊涂的南德方便面,走亲访友,家中常备,少了它的身影就像事儿不是那回事儿一样。我们小孩子喜欢干着吃,把辣椒面全部洒到面饼上,然后捂住袋子口,用一只手把面饼压碎,之后抓住袋口使劲甩,等面和辣椒粉充分拌在一起的时候,一小把一小把抓着吃,美味至极。 还有一种粮食,玉米,它注定是点缀。玉米粒一般喂鸡鸭鹅,玉米面一般喂猪。唯一放光彩的时候,是冬天炸玉米花的时候。 一种农村的老式爆米花机,把玉米放在一个装有压力表的铁桶里,架在火上烤,一边烤一边旋转,等达到一定大压力,把爆米花机一头放进一个长长的圆袋子里,师傅脚一踩手一拉,“砰”一声,爆开的玉米花就全部飞进袋子里了。 这些吃食重复在一日三餐,年年岁岁里。我们就是吃这些东西长大的。 (二)菜系篇 如果用花和叶作比喻,那主食就是片片叶,菜就是那枝头花,生活的点缀。 一直到现在,农民可以离开菜,但不能离开主食,两个馒头或一大碗面条可以填饱一个壮劳力的肚子,一碗菜,再多菜也撑不过半晌的工夫。 饿肚子的时候,人追求没有那么多,一旦温饱不成问题,人们就开始对生活有了追求,比如,开辟一个菜园子种点菜。 春天,莴笋,小香葱,油菜,夏天,番茄,茄子,黄瓜,豆角,丝瓜,苦瓜,葫芦,辣椒,油麦菜,上海青,茼蒿,韭菜,秋天,萝卜白菜是必须要种的,冬天就靠这些过日子了。时令的蔬菜,现种现摘现吃。 除了这些时蔬,农民也喜欢做点腌菜,比如,大蒜,阳历五月,鲜蒜可以用来腌制糖蒜,冬天,种蒜剩下的加塞小蒜瓣,剥皮之后,可以用来腌制腊八蒜,通体绿的那种。 煮过捂出来绿毛的黄豆与夏天的西瓜拌在一起就是西瓜黄豆酱,与红辣椒拌在一起就是辣椒黄豆酱。 有功夫的人家还会腌制红萝卜,白萝卜,辣菜,黄瓜等等。 你会发现,农村的每个县城都会有一家酱菜厂,这些厂里的产品就会成为当地的招牌特产。 在农村,可以吃的菜不仅有这些,春天的榆钱,可炒可蒸,香椿叶,配着鸡蛋炒,初夏的槐花,可炒可蒸,多余的槐花晒干之后,留作冬天包包子包饺子。 除了树上长的菜,野菜是我们的最爱,春天的(haohao)棵,荠荠菜,蒸着最美味。夏天的马蜂菜,茎秆是红颜色的,可蒸可凉拌,有益于降血压。 夏天,我妈喜欢摘些芝麻叶,在热水里煮一下,过多遍凉水,拌点蒜汁吃。有时也掐点红薯叶,下到面条里。 除了这些素菜,我们也会吃荤菜,吃的最多的是猪肉,家里养的有鸡,想吃的时候,杀一只,炖鸡汤,鱼肉不常吃,关键收拾麻烦,也不好做。 鸡蛋算是处在荤素中间的一道菜,家家户户每年春天都会养十几只小鸡,养到夏天会下蛋了,多余吃不完的鸡蛋会腌制一下。不过,我们这里人腌制的技术不是太好,坏的比能吃的多。 (三)瓜果篇 如果按照农村吃食的比重来算,主食排第一,蔬菜排第二,瓜果排第三。吃瓜果最多的季节是夏天,那时,地里种的有大西瓜,西瓜地里捎带种几棵甜瓜。 如果家里院子比较大,院中会栽桃树,石榴树,夏天吃桃,秋天吃石榴。 到了冬天,我们还可以用麦子,玉米,按照一定的比例兑换橘子和苹果。 (四)吃食文化 填饱肚子人才能活下去,粮食一直都是农村文化的图腾。 二月二龙抬头,农村会用草木灰在院子里打三五个麦囤形状的圆圈,我们叫打粮囤,春节时,我们会在粮囤上贴上“五谷丰登”的春联。手有余粮,心中不慌。 好像这么多年,农村吃食的味道偏好一直未变过。大鱼大肉不追求,平平淡淡的味道才是日常。从家常便饭里衍生出来的生活哲学,平平淡淡才是真。 大多时候,农民眼里只有庄稼活儿,吃饭是没有仪式感的。我们没有坐桌吃饭的习惯,村里的人喜欢蹲在自家门口,一手端菜拿馍,一手拿筷子,边吃边和邻居聊天。 如果非要坐桌,那就是有事情了,比如结婚或孩子过九天待客。早些年,办事之后撤下来的酒菜,主家会分别送给要好的人家一盆。酒菜香,这种味道一直让我记挂了很多年。 (五)乡村回望 这些关于吃的事情深深烙在了我这个农家儿女的心上,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我们开始不在祖辈世代经营的这片土地上讨生活了,但我们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aohuixianga.com/xhxxzjb/11549.html
- 上一篇文章: 冬天,我家就爱吃这馅料的包子,鲜嫩多汁又
- 下一篇文章: 郑州只有3张桌子的小破店,卖的是信阳热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