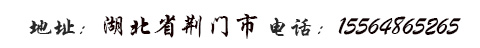武汉的宵夜正义图文汇
|
宵夜 江湖 在武汉街巷装修最简陋的民房里,往往藏着最生龙活虎的宵夜生活。武汉作为九省通衢之地,当地美食融合南北,受着码头商埠文化的感染,各种小吃宵夜数不胜数,深谙夜晚勾引食欲之道。 寻觅食味 19世纪60年代汉口开埠后,武汉码头的发展进入“大江经济时代”。随着租界建立和长江近代轮船运输的日益发展,临长江沿岸开始相继拓建一批近代轮运码头。清康熙年间,武汉因商业发达,成为四大名镇之一,而武汉的城市建制在民国时期才初步形成。 武汉最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何祚欢老师曾说:“武汉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极端不匹配,直到现在七扭八歪的巷子还是特别多,当年因为码头迁到这里的人可能随便就在哪里盖了所房子,人们居住环境很狭窄,养成喜欢在街上吃东西的习惯,稍微空旷一点的街巷,很快就会搭起早点和宵夜的摊子。这里对经济的重视远远超过政治上的,也因此市民的自治性非常强。”过早和宵夜成为武汉市民最生龙活虎的一面便不足为奇了。 提及武汉,不可不提“过早”必备的热干面,其中又以蟹脚热干面最为闻名。普通的热干面是蹲在街边就着嘈杂的招呼声呼哧几下便下肚,蟹脚面则要你必须坐在桌上戴好手套,少了几分生活气,又好像多了几分对食物的敬意。热干面依然是碱水面,比常见的面条略粗一点,撒上酸豆角,酱萝卜,炸酱,麻酱和葱花。蟹脚面的花蟹数量很多,酱汁浓郁,但是油分不厚重,辣味和花蟹的鲜味调和到正好。面条筋道,配上梁子湖中红白色壳的蟹,等待筷子去翻动着其中的美食秘密,一天的疲倦也随着一碗面下肚。 除了远近闻名的热干面,小龙虾一定才是武汉宵夜摊上永远的主角。 著名的小龙虾养殖基地潜江,距汉口不过一个小时的高铁车程,自潜江到武汉都有完整的小龙虾运输链,武汉流行的油焖做法最早也源于潜江附近的五七油田。 烧的红彤彤的小龙虾在灯光照射下显得清亮油润,没有辣椒、葱姜的遮挡,码放得整整齐齐地装好了一大盆,几十只大钳子直直地指着中央,显出一种诱人的魅惑来。做油焖小龙虾的厨师在放佐料上下手都极为阔绰,油里先下葱姜蒜爆香,接着各种鲜辣椒、炒好的干辣椒大把大把入锅,待呛人的香味滋滋入鼻,便把几百只小龙虾倒入锅中用力翻炒,再下入独门配料,让掩藏在虾壳下面的白色鲜肉更加入味。 拾起一只刚出锅的小龙虾,揭开红彤彤的硬壳,扯掉多余的触角,一块弓形的弹软虾肉完整地被剥离出来。汤汁已然渗进硬壳,一口吃掉白色的虾肉后,还会猛嘬一口虾壳里浓稠香烈的味道。 八角、香叶、香砂仁、山柰、白蔻、白芷、草果、丁香、小茴香……小龙虾在锅中同几十种调味料一同翻炒烧制的艰辛过程,仿佛都在嗓子眼里全力释放,使一顿宵夜也变得何等的浓墨重彩。 武汉的每一种饱腹之物,几乎都有人们约定俗成对应的“饮料”,如吃面窝喝豆腐脑,吃热干面喝蛋酒,吃豆皮喝糊汤米酒。 桂花糊米酒是武汉当地人家里的寻常食物,清淡可口,不会有小龙虾的热辣刺激,反倒显出武汉饮食上泾渭分明的态度。一锅浓稠的米酒点缀着星星点点的黑色桂花梗,飘着丝丝酒气,实在是一碗难得的心头好了。 真正的糊汤米酒在孝感,里面有软糯的小汤圆,由藕粉或者糯米粉勾芡,一碗下肚,暖流便在肠胃之间涌动,身外再冷寂也无妨了。 汤包、牛肉粉面、烧烤、炒菜、卤鸭脖、豆皮、牛杂、海鲜、锅贴……哪怕是寻常的糖水或者绿豆稀饭也足够耐人寻味。不顾姿态地在一家宵夜小店里坐定,甩开膀子猛扒几口,再灌一杯啤酒下肚,嗓子眼有辣感微微回升,仰天打嗝的那一刻仿佛才找到了久违了的生活真实感。 午夜凌晨,街角的流动推车前一对母子排着队等吃豆腐脑,满地扔着鸡爪骨头、虾壳、烧烤签和卫生纸的逼仄小巷,中年大叔汗流浃背地露天坐着,端起碗,将浓烈的汤底呼噜吞下,电动车载着货物紧贴着后背呼啸而过,代替空调吹来一阵凉气……这大概就是深夜排挡的魅力,坦诚直率,在简陋的民房里滋长出最亲切的家常味道,把八小时之外的深夜时光还给自己,是宵夜将白天的世界划出一个界限,打开一个新的时空。 声色街巷 武汉吃宵夜有个说法,“武昌司门口,汉阳腰路堤,汉口吉庆街”。现在,武昌有沙湖路,汉口有万松园,而吉庆街则更富特色。 吉庆街名声大噪多半源于池莉的小说《生活秀》,她曾如此形容道:“吉庆街是一个鬼魅,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无拘无束的漂泊码头;是一个大自由,是一个大解放,是一个大杂烩,一个大混乱,一个可以睁着眼睛做梦的长夜,一个大家心照不宣表演的生活秀。” 这条街总被夜晚的路灯唤醒,几千张简易圆桌板凳摆得密密麻麻,把不宽的街道也围得水泄不通,桌上牛肉粉小龙虾主打,各种卤菜火锅搭配,又有民间街头艺人驻场表演,家家都生意火爆,热闹非凡。30年,米,吉庆街用大排挡和街头艺人,演绎了一段武汉的民俗传奇,一度成为武汉民间文化的一个符号。 “过早户部巷,宵夜吉庆街。”这是一条靠近中山大道大智路口的的普通的街道,名字倒十分讨喜,叫吉庆街。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附近居民将小椅小凳小竹床摆在路边,开始“挖地佬壳”,到桌面摆到街上,小家小菜的“靠杯酒”。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个体餐饮摊点自发集结于吉庆街,原先只是寄生于“老通城”后面,后来靠这个老字号打出名气,逐步形成有浓郁汉味风情且名气越来越大的饮食文化街区。年开始进入繁盛时期,形成了以吉庆街为中心,包括邻近的交易街、瑞祥路、大智路在内的大排档市场。 然而,吉庆街的原始、喧闹与脏乱终究与现代化大都市的发展相矛盾,过江隧道的建设又把吉庆街的交通阻断,随着城市发展,狭窄的街道、脏乱的环境和不便的交通,使吉庆街这张“文化名片”黯然失色,让人们不得不开始正视和重新规划吉庆街未来的发展。 年3月,武汉市斥资进行整体搬迁改造,目标是将其打造成集餐饮、休闲观光、旅游购物于一体的国内品牌商业街,后因修长江隧道不得不在附近重建。年冬至,改造后的新吉庆街开街,次年三月正式开始营业,兴奋的商家和市民对新吉庆街充满了期待。 然而,新吉庆街开张不足两月,14家餐饮企业就已支撑不住亏损,陆续撤离夜市经营。因为普遍亏损,到年,原先进驻的近20家餐厅,仅剩四家规模餐饮企业,以及一楼的馄饨店。到年,这几家店也先后停业,最后只剩一家馄饨店。 惨淡经营的背后,是新吉庆街运营方和业主陷入纠纷的管理风波:年3月,武汉同丰商业公司退出新吉庆街经营,暂由江岸国资公司派驻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同年5月1日晚,所有的餐馆均未开业,店里漆黑一片,大门紧锁,人去楼空。此时距其年12月22日开门迎客,仅4年多的时间,“吉庆街”不但没有改造升级后的名声大噪,反而使这块武汉夜市老招牌黯然失色。 “吉庆街有一块石头,刻着我写的题记。那是为新吉庆街开张写的,开张时候我去一看,题记被刻在背面,人在大街上根本看不到,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预兆不好,觉得新街很难再火。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一向看重细节。这个细节至少说明,这个街做事情不符合客观规律。大凡不符合客观规律的事情,迟早做不下去。”池莉听闻吉庆街惨状时,对此早已有所预感。如今,这块刻着“吉庆街”字样的石头,仍摆在街道入口,默默地注视着新吉庆街的来来往往。 在当地人看来,吉庆街改造后的衰败跟街道的规划设计不无关系。过去的吉庆街多是露天排挡,烟熏火燎,因陋就简反而人气颇高;新街把餐桌都收进室内,精致整洁,深居二楼的高档餐厅多了,但同质化严重,失去了原本的汉口风味。文化才是建筑的灵魂,如果没有与吉庆街相匹配的汉口文化,再堂皇的建筑也给人空荡之感。 这个国庆节,当我们来到吉庆街时,景象已全然不复萧瑟,反是游人如织,家家爆满。华灯初上时,这里油烟锅铲、二胡喇叭、风琴吉他,土洋混杂,活辣生香,一直闹腾到深夜,武汉就在这里呈现出一幅鲜活的市井百态。红墙回廊,挑檐窗花,游人踩着凹凸不平的路面,穿梭于清末民初风格的建筑群中,耳旁尽是食客喧闹与管弦丝竹之声。一阵浓烈孜然辣椒香味传来,等待着被红油滚烫浸润的竹签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色彩。胖胖的中年男子,坐着露天的塑料板凳,轻车熟路地拿出调味碟。有些人没占到位子,索性坐在树边小台吃着烧烤,瞪大眼睛用方言谈论着生活琐事,有新的人要来坐,赶忙说“你给人家让个位子”。 有人摇着蒲扇,有人抱着孩子,许多外地人来到吉庆街,并不仅仅为了吃,多数是冲着这里汉味十足的“民间艺术”。在吉庆街吃夜宵,不时有背着吉他或是手持各种其他乐器的街头艺人,拿着点歌单邀你点歌,民间小调或者流行歌曲,他们都能即刻为你演奏。风味小吃,满桌佳肴,乐声贯耳,人流如织,吉庆街弥漫着一种美食营造出的武汉独有的城市气息,一种平实热闹的烟火味道。 除了吉庆街,武汉的夜宵地图上还有许多不可不去之处。万松园是武汉蒸虾最集中的地方,这里分布着大大小小百余家餐馆,处处可见火红的虾壳和为小龙虾而排起长龙的食客。外地人来武汉,大多会选择去户部巷转转,位处武昌中华路临江的户部巷是武汉最有名的“过早”一条街,也是反映武汉市民生活最生动的一条街。街道长不过米、宽不过3米,却集中了几十种特色小吃,不可不谓是“唤醒”武汉的街道。鸭脖飘香的精武路,称霸“苍蝇大排档”的新桥街,包揽名校学子口腹之需的广八路……夜风熏得游人醉,七扭八拐的巷子,往来行人如织,武汉的不夜天里还有食客继续着一轮又一轮的美食寻访。 平民的 英雄主义 王老板是在吉庆街摆摊卖烧烤的摊主,每天在浓烈的烟熏里卖烧烤的他,收摊后身上总有一股很浓的碳火气。 吉庆街有一条小路是属于露天的烧烤摊主们。天已暗暗地沉了下去,橘黄色的灯光打在油腻湿滑的石板路上。戴着围裙的王老板,动作麻利地给顾客们烤着面筋和猪蹄。他与我们聊天时有说有笑,做起烧烤来依然仔细,一边检查着食物的熟度,挨个翻烤;一边均匀地刷着酱料。问他为什么不做好再卖,可以节省时间,他笑着摇头,用浓浓的武汉口音说着“那要不得,要现烤的,不然人家不要呢,食品管理局也有要求。检测,做标本,一个星期之内有问题就会出来一个报告。” 王老板今年四十余岁,和他的妻子吴春梅前几年一起来武汉卖烧烤,现在在吉庆街一个月生意好的时候能挣一两万。90年代,他们在老家的商场做服装销售,后来遇上体制改革,被迫下岗。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四处找亲友借钱,在一个小区里开了一家小超市却最终因经营不善倒闭,亏损了30多万元。他们有一个在武汉读大学的儿子,夫妻俩每天早出晚归没什么时间陪他,“他很喜欢到处去旅游,不过平时还去星巴克做兼职,算是自食其力吧。”他们很舍得给儿子花钱,买衣服、买相机,缴纳不菲的艺术学习费用。 说起烧烤摊的经营,吴春梅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在她看来,要在夜市把烧烤店做大,就一定要做成品牌营销的模式,“像这里的老字号,蔡林记,四季美,老通城,都是因为把品牌作响了才能吸引那么多客人。” 吉庆街的店面租金是元一个月,物业费元一个月,生意不好的时候对摊主们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对于将来,她很希望吉庆街能加大宣传力度,让游客们不只知道户部巷,也能到吉庆街感受一下老汉口的街头味道。 前方传来了热闹的的萨克斯乐,循声而望,一位老艺人站在人群中纵情奏乐。一曲吹罢,老艺人又唱起了美声,越来越多的人拍照围观,食客们跟着鼓起掌来,将大排档的气氛逐渐推向高潮。老人来武汉四十多年了,以前是文艺兵,后来在港务局下岗后,就来到这条街上卖艺为生,已经十六载了。 另一位身形清瘦的老人在热火朝天的大排档里显得极为不衬,拿着一把二胡,一连问了好几桌客人也没能被邀请拉上一曲。 今年70余岁的王永才老人是武汉本地人,自九岁开始学习拉二胡,在武汉和重庆涪陵两地从事机械工作生活了几十年,退休后又回到了武汉。他一直十分热爱演奏二胡,在外地工作也一直把二胡带在身边。 起初他的老伴和两个儿子都不太同意他来吉庆街夜市做街头二胡艺人,可实在拗不过老人喜欢拉二胡给别人听,也体谅他想补贴家用的心情,只好作罢。老人一般在晚上七点到九点半出来拉二胡,那些更年轻的艺人则往往持续到深夜十一点才收工。夜市里受欢迎的总是那些会抱着吉他、弹唱流行歌曲的年轻艺人,像王永才这样演奏传统民乐的老艺人,生意总是比较冷清。拉一首曲子20元,一个台子包场的话会有元左右,不过这样的情况几乎没有。平均下来,王永才老人一晚上能挣几十元,一个月有两三千元的收入。 他说,前几年的时候有很多记者来吉庆街采访民间艺人,他很抵触,怕被别人看见就像“越活越栽了”。现在他非常希望能有记者来报道逐渐受到冷落的传统艺术,“以前吉庆街有五个搞传统乐器的班子,二胡、琵琶、笛子什么都有”,后来艺人们纷纷离开另谋生存,如今这里只剩下零星几个人还在演奏民乐。 如今,吉庆街的街头艺人每个人在上岗时都会在胸前佩戴一个由街道办事处颁发的“街头艺人证”,无证则不能在街头表演,每一位艺人每月还需要向街道办缴纳元管理费。 90年代起,令吉庆街闻名的并不只有这里品种丰富的食物,更是吉庆街丰富的民间节目,有民歌、流行歌曲、传统乐曲和京剧、汉剧、楚剧、黄梅戏、豫剧、湖北大鼓、评书、笑话等,一首歌或一个曲子十块钱。当年吉庆街的多位艺人中有四位佼佼者被评为“四大天王”,他们分别是“麻雀”、“拉兹”、“黄瓜”和“老通城”。 “麻雀”是第一个到吉庆街来卖唱的艺人,一把二胡,自编自唱自演,风格诙谐生动;“拉兹”扮相怪异,独树一帜,擅长双簧,表演逼真投入;“老通城”以什么歌都能翻唱的老通城广播电台出名;“黄瓜”善演小品,声线自备女声模式,自成一派。他们的最高成就是在年,全球著名的Discovery探索频道播出了一部讲诉他们故事的纪录片,把吉庆街艺人们称为“中国街头的卓别林”。 至年吉庆街重新开张之时,几百人的演出艺人四散东西,早已不复当年鼎盛景象。现在的吉庆街气氛大有回转,仍有许多街头艺人每天晚上吹拉弹唱跳,给无数食客带来欢乐。 张冬至也是一名街头艺人,十二岁来到武汉,如今已在武汉待了九年。他擅长打击乐,即便用筷子敲碗也能打出律动的节奏。表演到高潮,他还配合着音乐玩起了beat-box,赢来路人一片欢呼。 游人是夜市的主力。长沙理工大学的陈泽宇趁国庆假期约上了同学来武汉游玩,在他的眼里,“吉庆街有点长沙坡子街的感觉。”同行好友李宇同买了一大碗牛骨汤,“平时因为学习比较忙,很少吃夜宵,听说这边夜宵很不错就想来试试,感觉长沙比武汉还要辣一点。” 武汉的宵夜风情不可想象之精彩,威猛之物,通通入嘴,市井生活的乐趣大概就在于此了。高楼之间往来的全是面目不清的陌生人,反是街巷之间方能呼朋唤友,高谈阔论,长凳与火光的明灭引出酒后的一声声喟叹,这也许就是对现代城市生活的隐喻。清秋已至,约上三五好友,完成一次武汉宵夜检索,感受一场人间烟火吧。 文 记者团朱雯卿王之玉潘楷玲 图 记者团马金瑞郭哲良李沁颖 见习记者胡家轩邱芊陈淳一 编 记者团文露漪 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kushens.com/xhxxgpw/776.html
- 上一篇文章: 荐号中医告诉你20个健康金标准,这样做最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