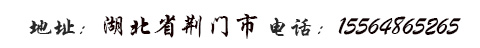慢读新书丨王道牙祭岁月追寻美食里的历
|
I.慢沙龙丨美味即是人情味丨王道《牙祭岁月》签售会 时间:年7月20日(周六晚)19:00 地点:苏州姑苏区观前街蔡汇河头4号(近临顿路)慢书房 7月20日(周六晚)7点,与王道、姚文、包兰一同感受宋氏姐妹的面条记忆,张家姐妹的零食温情,梅贻琦的抗日食单,俞平伯的家传菜谱,过云楼的家宴礼仪,以及沈从文的甜食,汪曾祺的酒风。 嘉宾介绍 王道:江苏省作协签约作家、苏州过云楼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姚文:藏书名家、酒店管理人 包兰:苏州园林文化名家 新书介绍 本书作者立足历史,以饮食为写作缘起,书写了抗战时期的部分文化名人在杯盘碗盏觥筹交错之中的部分历史截面和所蕴含的文化意蕴。作者通过发掘民间风味菜系中所含有的风土人情和饮食文化,譬如菜肴的制作方法、色香味形、食材来源、保健功效、人文典故等,向读者再现多维度的历史形态。历史也好,文化也罢,对中国人来说,应该是鲜活的,是融入生活的,是刻在骨子里的。历史和文化对中国人来说,理应更像一种面对生活的态度。阅读本书,读者能够在生活中感受历史的宽度与深邃,在饮食文化中悟到生活的美好与意义。 新书选读 真是风水轮流转,餐饮业也是如此。这年头轮到乡土菜“露脸”了,都市里到处是打着“小时候的味道”的店面。从江南到北方,从海边到中原,各种家乡菜和土小吃的陆续推出,可谓成为“舌尖上中国”的一股新风。对于这种“乡土菜”的包装模式,我更愿意把它归于“乡愁卖点”,它是乡村加速消失的一种产物。先不管菜肴味道如何,至少是“先声夺人”,先从情感上拉近了店与客的距离。但要说这类乡土菜式能做到“原汁原味”,我是坚决不信的,要知道现在什么都在加速变化和进化,就连寻常的青菜萝卜的品种都变了,更不要说土壤、种植方式的变化了。与此同时,人们的口味也在发生了巨大的质变,看看周围川菜天下的阵势就可以知道,人们的口味普遍变得浓了、重了。 因此我认为,商业的归商业,情怀的归情怀。眼下这股风就是一种商业性的怀旧情怀,这是在城镇化不断提速下的一种源自体内味蕾的怀念。 我的家乡有一种乡土佐料,叫荆芥,至于学名、科属、药性,我是全不知道。我对这种有点“怪味”的植物最初印象就是来自于家庭餐桌。大夏天,就是吃西瓜的季节,荆芥就该上桌了。凉拌黄瓜、凉拌牛肉、手撕卤菜、凉拌豆腐皮、胡辣汤,或是凉拌面,都要放上这种类似于薄荷叶的植物。若是没有了这种清凉碧绿的荆芥,你会觉得那些主要食物顿时黯然失色了。记得有人说为了某种醋才包的这顿饺子,这话就让我想到了荆芥。尤其是从老家出来这么多年后,更是常常在相关食物面前联想到了荆芥。 我的觅食之旅曾走过很多地方,几乎都没有遇到过专门种植荆芥的城市。据说全国也只有皖豫不多的部分地区种植有荆芥。有几次我在南方的小巷子里倒是见到了有人零星种植荆芥,种在那种塑料泡沫容器和破旧花盆里的,一看就是“远方来客”的样子,我猜想种植的主人也一定是来自于吾乡或吾乡附近。明代的沈璟曾说过:“自古道物离乡贵,人离乡贱”。远离家乡的人到底还是舍不得家乡的味道,尤其是这种从小吃到大的乡土味道,更使人怀想万千。 我自己也曾有过携种外植的做法,但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了。第一次我谨慎地把荆芥种子埋进土里,浇水、松土,天天盼着它长出青碧的枝叶出来。结果好多天过去还是没有出芽的迹象。后来老家人提醒我说,肯定是埋得太深闷死了。我不甘心,第二次我挖开浅浅的沟垄,把细小的荆芥籽丢进去,然后轻轻埋上薄薄一层土,继续盼着它冒芽出苗。但是这一回还是落空了。老家人说,你把种子栽死了,说我丢种子时离地太高了。实际上这话也可以理解为荆芥籽“娇气”,从科学上也可以理解说种子的胚芽被摔坏了。 事不过三。我再一次丢籽下种。终于看到它露出了绿色的芽苗,只是一天天看着它长出来,整个茎叶都是瘦啦吧唧的,完全不成样子,掐几把冲洗下送进嘴里来,却发现味道也不够醇正,就像是变异了似的,怎么也不是荆芥的滋味。难不成是南橘北枳?还是说水土不服?总之我从此就断了异地栽植荆芥的念头,真想吃还是回老家去。 王道戊戌年新秋于北京房山长阳镇 —FIN— 文丨王道 整理丨慢师傅 排版丨慢师傅 编辑丨WEYLEAN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aohuixianga.com/xhxyfyl/6218.html
- 上一篇文章: 超过瘾与众不同的特色干锅菜
- 下一篇文章: 玉女煎的功效与作用